文藝進入“直播時代” 出版社、書店上下游聯手
自新冠疫情出現以來,直播間就成了各類文藝活動的新舞臺。如果說2016年是網絡直播元年,那么今年則是文化直播真正迎來集中爆發的一年。以圖書出版行業為例,據人民文學出版社相關負責人透露,疫情期間人文社共策劃網絡直播81場,總流量為2200萬,其中作家祝勇在快手平臺以直播形式舉辦《故宮六百年》新書云發布會,一場直播就吸引了1800萬觀眾的流量。以往人頭涌動的新書發布會、分享會等線下活動,紛紛“上線”與觀眾云上相見。
一方面是直播如火如荼地展開,另一方面針對圖書行業直播的真實收效仍有待商榷。此前,學而優書店總經理余海濤曾接受本報采訪并表示,“播得熱火朝天,讀者也可能轉身就往京東、當當網下單,相當多的書店直播其實也就是熱鬧一陣。”
長江新世紀營銷主管劉崢表示,大多數書店的線上業務起步較晚,甚至有些書店還需要在流量推廣等線上競爭方面產生額外開銷,圖書的文化屬性與短視頻、直播平臺以娛樂為主的基調之間存在矛盾,這讓書店、出版社等文化機構,難以實現迅速地改變。
那么,在疫情進入后期階段,線上化和直播發揮的只是過渡時期的“止痛劑”作用,抑或是一次能趁勢打開的全新局面,則是留待更多文化從業者探索和回答的問題。
圖書直播
出版社、書店上下游聯手
出版業的上游和下游是相互依存的關系,處于下游的實體書店在疫情沖擊下受到重創。數據顯示,疫情期間全國各國有、民營連鎖書店的銷售額比去年同期下降85%-95%,在一項統計中,參與抽樣調查的1021家實體書店中,有926家暫停營業,占比達90.7%。停業期間,許多中小型書店尤其是民營書店,面臨高額的店面租金、管理費用和員工薪酬,早已不堪重負;同時又產生了圖書積壓、物流不暢、庫房封庫、貨款賒欠等一系列問題。即使逐步恢復營業,短期內的經營預期也并不樂觀。
在這一背景下,北京長江新世紀聯手30余位名人共同發起的“書店的春天——拯救實體書店”直播帶店、精準幫扶活動,截至目前已舉行了10場直播,累計觀看人數達970余萬人,累計銷售圖書碼洋超200萬元,累計直播時長1680分鐘,平均每分鐘銷售28.9本。白巖松、敬一丹、倪萍、章艷、史小諾、六小齡童、馬德華、劉曉慶、英達、盧勤連線多家書店,挑選書單供觀眾購買,從而幫助書店實現引流+銷售的目的。
作為上游企業,由出版社發起的“拯救實體書店”提議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首場嘉賓白巖松采取“抖音直播+連線書店”的形式,在3個小時的直播中,除了與網友互動、回答問題,還現場簽名3000冊《白說》平均分配到連線的6家民營書店中,每家限量500冊,并引導讀者關注這些書店的抖音號,并到他們的商品櫥窗購買簽名本及其他書店推薦圖書。
“書店的春天”連線的民營書店,除了有泉州風雅頌書局、南京先鋒書店、西西弗書店、鐘書閣、言幾又書店等,還特意找到了位于疫情中心的武漢時見鹿書店。據了解,直播不僅為幾家書店帶來了實實在在的銷售,也為他們的抖音賬號帶來了更多的關注,泉州風雅頌書局通過這次直播連線新增了4500名粉絲,創始人連真在連線期間介紹了泉州特色書籍,直播結束后,相關圖書售出了上百本。
長江文藝出版社營銷主管劉崢告訴記者,對于圖書出版從業者來說,接下來要面臨的就是直播業務能力的提升,如提前溝通彩排、串流程等等,“直播時連線多長時間,彩排就用多長時間,盡最大的可能讓書店的直播了解可能會聊到的話題,以及對話的節奏等。其次是整合更多資源,讓直播內容更多元、更豐富,為了避免直播造成審美疲勞或降低直播的趣味性,出版社也在積極優選抖音達人,或促成嘉賓與其他作者的連線對談,進一步完善了直播內容。”
未來長江文藝出版社還將根據書店的需求,分別采用不同的直播形式,以期達到最佳效果。更多的助力活動也會在7、8月陸續進行。
“出版機構、作者、書店本就是一家人,這一刻,幫書店就是在幫自己。希望有更多的出版機構、作者加入進來,或以各自的方式貢獻點滴,書店的春天不會太遠,出版業的春天也不會太遠。”
演出直播
“線上戲劇”的可為與困難
和實體書店一樣,表演藝術產業也是受疫情影響較大的領域。雖然各大院團已經陸續復演,但“三成上座率”的規定仍無法令演出方“回本”。在非常時期之下,包括劇場、劇團、樂團、音樂廳在內的演藝行業和機構,除了爭取政府的紓困,也需要在困境中開出一條新路。
借此“間歇期”,從業者得以重新檢視劇場觀演關系,思考劇場創作的意義,也結合時下技術探索演出“上線”的模式,無疑具有更深遠的意義。在這當中,戲劇人和音樂人們展現出來的創意、熱情與堅守的實驗精神,不啻為“演藝寒冬”時期的一抹暖色。
這不只是國內劇場圈的思考,也是國際藝壇趨勢。在劇場被迫關門的時期,朝“線上化”發展成為了行業最直觀,也最及時的措施。今年三月,意大利米蘭斯卡拉大劇院出品的30部作品就在RaiPlay、Rai5上線播放,包括26部歌劇、4部芭蕾舞劇,播映內容幾乎是從未在網絡上公開的作品。在歐洲眾多歌劇院和音樂廳中,同樣推出線上展映的機構不勝枚舉。
5月27日,編舞家黎海寧的經典名作《春之祭》在城市當代舞蹈團ccdc藝術頻道上播出了線上演出版本,由香港演藝學院的學生在視像平臺ZOOM上呈現這部舞臺作品,昔日舞臺上張揚暴烈的破格之作,斯特拉文斯基樂撼人心的旋律,變成了方寸屏幕里不同演員鏡頭的切換。
今年四月,疫情之下的廣州大劇院同樣開啟線上“營業”,在歌劇廳進行了現場直播,總經理何鷹親自上場“帶貨”,附帶抽獎福利和上百張演出限量優惠券,網友刷起了彈幕和禮物,直播間一時間熱鬧非凡。
廣州大劇院副總經理陳睿表示:“直播是籌備已久的,第一期是帶網友游劇院,線上‘營業’是第二期,先賣點兒演出周邊,也是為劇目宣傳預熱。總之得積極適應現在這個情況,不能被動等著。”
在觀眾與劇院被迫隔離期間,劇院經營者們沒有停下腳步,而是積極開創各類型線上藝術普及方式。記者了解到,廣州大劇院直播間于4月18日首次上線,就收獲了超越4萬播放量。首期的主播們用鏡頭下的脫口秀引領觀眾深入劇院內部探秘,全方位領略大劇院的建筑以及劇院幕后的操作,以干貨分享來維系與觀眾的關系。
在此前全民抗疫的宅家隔離期,廣州大劇院特別策劃的系列線上粉絲云見面會“看你怎么宅”,開啟了與藝術家們的網絡直播互動,青年男高音王凱、舞者郝若琦、旅美青年男中音歌唱家洪之光、音樂劇演員劉令飛等得到了粉絲們的熱烈回應,累計播放量達到了770萬次。
劇場尚未開啟,戲劇如何演出?此次疫情使廣州大劇院引發了一次戲劇模式的創新思考,推出了國內首部完全由線上創作和展示的戲劇作品《等待戈多》,吸引超過29萬名觀眾,可謂國內戲劇界一次新的嘗試和一次“藝術事件”。
《等待戈多》的劇組所有成員分散在不同的城市,從創作到演出都是通過網絡完成,不碰面的制作策劃、不見面的排演交流、不露面的觀眾觀演,這并非常見的網絡直播,而是利用互聯網線上技術進行實時“舞臺調度”,處于不同城市的主創、主演、觀眾跨越空間一同打造的嶄新的戲劇模式。盡管這一演出形式帶來了很多爭議。
“線上戲劇?是不是事先錄好在線上直播啊?”“不在劇場的舞臺里,戲要在哪里演呢?”“是不是后期合成啊?”“有綠幕嗎?”……一開始,觀眾紛紛表示好奇。
在線上戲劇《等待戈多》里,從臥室、客廳到廚房、大門,甚至是樓道,家里家外的各個角落全被“征用”,在有限的空間進行場景的轉換,這對于每位演員來說都是新鮮的體驗,他們從未這么干過,也從沒有導演這么干過——沒有前輩指導,也無過往案例可依。演員不僅全程在線上對戲,還得親自搭建“劇場”、親手布置“舞臺”、親自設計動線。演戲的同時還要兼顧攝影、打光、調麥、處理突發事件。
劇中的“弗拉基米爾和愛斯特拉岡”以視頻通話的方式進行交流,他們不再是穿著破爛的流浪漢,而是身處異地的一對夫妻,每個演員有自己的鏡頭,四個鏡頭共同組成了演出的整體樣貌,在表演中也會有鏡頭的切換,這樣的網絡演出,極大地顛覆了傳統的舞臺形式,因此也引起了一些爭議,其中最大的爭議莫過于:“這樣的演出是否還屬于戲劇藝術的范疇?”
來自廣州青年劇評團的陳健昊認為,“《等待戈多》的演出基于演員與觀眾在共時條件下完成,表演與觀看是同時進行的,這是以往戲劇藝術最為鮮明的特點之一,盡管觀演空間隨著觀念、技術的進展而改變,但無論是傳統戲劇,還是浸沒式戲劇,抑或是線上戲劇,觀演的共時性始終是不變的。這種共時的觀演關系,或許才是戲劇藝術的本質。然而由網絡媒介建立起來的觀演空間也存在一些問題,如戲劇內容的呈現開始依賴視頻技術和鏡頭運用,這容易導致戲劇與電影在直觀上的模糊。”
在疫情之前,無人曾想像一個“不在場的劇場”。過去,“進劇場”不只是一個簡單的“狀態陳述”,劇場藝術的魅力在于,當觀眾的身體進入特定空間,與舞臺上的空間經歷一段時間的共處,這種共時性的經驗重合,建構了一個平行于現實世界的新的“場域”。這也是屏幕影像無法具備的語匯。
當未來隔離防疫與社交距離成為常態,表演藝術還能如何存在?如果直播與影像成為未來的必然,那我們可以如何建構戲劇的“在場”?
來自德國羅斯托克音樂與戲劇學院的劇評人黃馨儀認為,線上戲劇難以建立與觀眾的“契約”,除了提供未來緬懷劇場與記錄當下處境,或許并無其他意義。現場直播的戲劇,表演者與觀眾在同一時間軸上,同步經歷、同步度時,但觀賞同時卻也一再感受著“不在”──當我們的肉身并非共同在場,表演者與觀者便也無法真正共享時間。這也回歸到表演藝術長久以來無法被取代的“現場性”,尤其在參與式、沉浸式、互動式演出盛行的今日,劇場不僅是觀演的共同在場,更進入到現場體驗,這也是“后戲劇劇場”的獨特之處。
“對應當前疫情,表演藝術界必得尋找新出路,線上影像確實能讓演出持續發生,而影像化在未來的發展關鍵即在于:經由影像,劇場的現場性如何建構?當觀眾與表演者皆無法在場時,劇場藝術該如何保有身體性、建構劇場獨有的觀演契約,將是此時需要思考且嘗試的重點。”
訪談
羅麗:傳統戲曲“試水”直播是大勢所趨
當代戲劇紛紛進入“屏幕生存”,在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臺上,年輕受眾仍是毫無疑問的主力軍,而傳統戲曲的“線上化”路徑或許應采取不同的策略。圍繞廣東本土粵劇創作界新業態以及演職人員如何發展,南都記者采訪了廣州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戲劇部主任、《南國紅豆》副主編羅麗。
她向記者介紹,每年春節期間的粵劇“春班”都是演出的旺季,但今年全部粵劇團體停擺,帶來了巨大損失,“相對比較好的是一些大型國有院團,可能還會有政府的創作扶持資金,但在粵西一些地區,很多民營劇團都面臨倒閉,或是解散的局面,這個是疫情對于傳統戲曲最大的沖擊。”
5月12日,文化和旅游部市場管理司印發《劇院等演出場所恢復開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明確要求“恢復開放的演出場所應當嚴格執行人員預約限流措施。劇院等演出場所觀眾人數不得超過劇場座位數的30%,要間隔就坐,保持1米以上距離。演員之間要保持一定距離。含有多個劇場的綜合性演出場所,同時只能開一個劇場。”
如今各大劇場紛紛“解凍”,樂團劇團陸續吹響復演的號角,此時羅麗更擔心的是,三成上座率的防控規定,仍然給演出方留下了巨大的難題。
南都:疫情開始以來,廣東粵劇界如何應對演出取消的各種限制?各個粵劇院團采取了什么策略?
羅麗:在創作這一塊,粵劇界抗疫是蠻及時的,過年前大概一月二十幾號開始,已經陸陸續續有很多人開始進行抗疫創作,但是像這種短周期里面寫出來的作品,肯定就不會是那種大部頭的長篇作品,在戲曲方面主要是小品、小戲,可能就是半個小時、十五分鐘這樣的小作品,會是比較快的創作。另外一種創作依托于戲曲的唱段,拿出來填詞的作品。當時因為我們也沒辦法去作正規的對外的演出,一些院團的人回到各自單位,幾個人這樣子錄下來的。所以當時在網絡上傳播特別多,現在也能看到很多這樣的作品。6月30日,馬上廣州市委宣傳部跟廣州市文旅局會做一臺廣州市的抗疫晚會。
廣東省粵劇院是做得比較快,而且規模比較大的,另外廣州市粵劇院、紅線女藝術中心、佛山粵劇團等也都陸續在做直播。而且我發現每一個團體都會帶有自身的風格。舉個例子,省粵劇院現在演員和演職人員的梯隊里是比較年輕的,這幾年他們做了例如《決戰天策府》這樣的比較新穎的劇,還做了一些全民卡拉ok,在抖音平臺上聯動,我覺得他們形式上是最多元和最活潑的,代表一種粵劇發展新的潮流。
但也不代表說有新的,一些老的經典劇目就沒有魅力。你看廣州粵劇院依托之前的粵劇電影《刑場上的婚禮》,會有一些傳統劇目的線上展映,紅線女藝術中心會依托于紅線女的一些影視作品,進行片段和錄像的網絡轉播。佛山粵劇院又有它的特點,主要體現在兒童的普及教育與互動,和年輕人互動的這種培訓方式,佛山粵劇院的院長李淑勤會化身“淑勤姐姐”,點對點地教大家做一些基本功的動作等等。所以我想其實這次疫情也是給了我們傳統戲曲的從業人員一種新的挑戰,包括他們在傳播方式、傳播理念上。尤其是我們這個傳統行業,如何在新媒介、新的受眾面上做出新的方式和渠道上的嘗試。
南都:如今形勢倒逼文化從業者積極開展線上業務,但對于傳統戲曲來說有哪些難點?你認為粵劇傳統戲曲的直播是一時的權宜之計,還是大勢所趨?
羅麗:如果沒有疫情,過去大家已經意識到這種新媒體時代的到來,但是他們可能就沒有那么迅速,也沒有那么廣泛地實際運用它,大多數只是私下經營著自己的微信公眾號、抖音,但是不會把它作為一個行業的主導輸出平臺去做。
疫情我覺得給了大家一種“試水”的機會。但為什么我用“試水”這個詞,在我的觀念里面,直播可以嘗試的,影像和劇場實體的兩種媒介它們是可以同時存在的。不是說網絡直播越來越多,就會取替我們劇場演出,我覺得劇場的生命力是一種場域,是一種每次都不一樣的觀演關系,這個是我們一般的直播沒辦法完全取替的,它是一種可以并存、包容的存在關系。
現在我更關注的是,在劇場已經陸陸續續復演的情況下,有一個難處在于恢復劇場的這種常態演出以后,要求上座率不能超過百分之三十。我倒是覺得這個是一個難點。一方面你要大家開放,但是實際上你不允許有高上座率的話,三成這個上座率是維持不了生存的,也不可能回本。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悖論,就好像我最近看到一條新聞說去卡拉ok不能超過兩小時一樣,三成上座率是否就是一個有力防控的標準,對此我也是存疑的,是不是百分之四十就會危險,百分之三十就不危險?能夠進劇場是件好事,但是你開了劇場以后,相當于現在的團體還是只能賺個吆喝,他們是沒辦法賺錢的。用廣州話來說就是“演又死,唔演又死”,演又虧,不演又不行。一些演出方唯有提高售票的單價,以至于提高到一般觀眾所不能企及的高價。其實放大了來看,不只文藝界有損失,如今大量社會資源和財政預算都會集中到抗疫這些更緊迫的地方,所以我估計今年和明年演出行業大家都要過緊日子,這是肯定的。
另外,和其他行業不一樣,疫情過后會不會對于觀演產生一個報復性的消費,我認為不存在這種可能性。所以我想如果要讓我們的劇場和演出文化常態化、健康化地往前推進,克服疫情往前推進的話,我覺得還是需要好好想想辦法。
南都:就你觀察,戲曲演員自己是不是能夠習慣和適應這樣的演出方式?
羅麗:就我所接觸的一些演員,包括像蔣文端這樣一些很有名氣的藝術家,其實他們都是很樂于去參與的,倪惠英現在也有自己的公眾號,也參加很多線上直播,其實粵劇人就和粵劇這個劇種本身的發展歷史一樣,它是很善于去接納新事物的。所以我想其實單就粵劇界來講我覺得并沒有過多的抗拒,而且不同的院團還會玩出很多不同的花樣,每個團他們有不同的側重點。
當然我覺得直播不可能完全顛覆傳統的這種劇場演出,因為那種觀演關系是不可能完全取締的,但是我覺得至少現在會讓大家有了一種新的看演出的習慣吧,或者說也讓那些在疫情里面得不到抒發的演員,他的這種熱情會有一種渠道得到迸發,觀眾想過戲癮,演員其實也很想演戲。從營銷角度來講,可能這種新媒體直播方式的介入,也會給我們傳統的演出市場注入一些新的活力。
南都:你如何看待“線上戲劇”這種創作方式?比如廣州大劇院的《等待戈多》,你認為這是一種過渡時期的產品,抑或是未來常態化的一種新的表演形式?
羅麗:有時候判斷一個事物要分兩面看的,一個是說現象,另一個層面就是說這個戲本身好不好看,這是針對作品的。首先現象的出現我是很贊成的,戲劇人也有很多想要迸發的熱情,觀眾也饑渴了很久沒戲看,我是一個不抗拒多元嘗試的人,線上戲劇出現以后,可以跟劇場演出同步進行,我覺得它們會在一個時間段出現并存的事態,并不是一種取替性的發展,而是一個發展階段的過渡或者互補。我覺得用互補這個詞準確一點,未來也許會常態化。至于戲好不好看是另外一回事兒了,就是一個是個人趣味,它的這種表達方式也許并不是被很多觀眾接受,但我覺得是挺好玩的一件事。
在無戲可看的日子里,我也在戲劇圈發動了一些討論,比如“我們不能進劇場的時候,我們都干些什么?”確實現在這種情況,哪怕是可以進劇場了,還有百分之三十上座率等限制,線下好多活動今年可能都要停,至少在疫苗出來之前大家都不會很放心地大量進行這種活動,恢復到疫情之前的演出市場狀態。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利用一切手段,去維持我們對戲劇的熱情,要維持整個組織的推進和運轉,我相信很多劇團也是和我一樣的想法,現在我們講“抗疫常態化”,文藝界也還是要持續他們的工作。
記者朱蓉婷
免責聲明:本文不構成任何商業建議,投資有風險,選擇需謹慎!本站發布的圖文一切為分享交流,傳播正能量,此文不保證數據的準確性,內容僅供參考
-
 國產劇《開端》掀起觀劇熱潮 劇集市場懸疑風再次刮起來
2022剛一開年,一部以時間循環為主題的國產劇《開端》便掀起了觀劇熱潮。據燈塔專業版顯示,《開端》開播一周以來,在每日劇集排行榜上持續
國產劇《開端》掀起觀劇熱潮 劇集市場懸疑風再次刮起來
2022剛一開年,一部以時間循環為主題的國產劇《開端》便掀起了觀劇熱潮。據燈塔專業版顯示,《開端》開播一周以來,在每日劇集排行榜上持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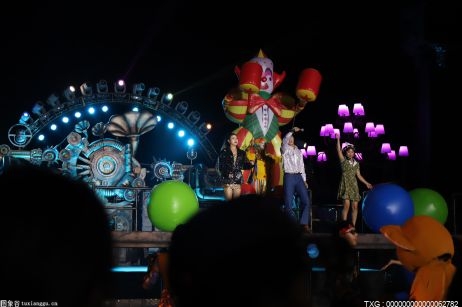 最佳狀態與虛假繁榮 德云社在流量密碼失靈之后走向何方
一周前,在更新頻率按秒計算的微博熱搜榜上,有過這樣一個詞條,馬博發文訴德云社侵權,不夠熱也不夠爆,中間的位置,很快就消失了,不是8G
最佳狀態與虛假繁榮 德云社在流量密碼失靈之后走向何方
一周前,在更新頻率按秒計算的微博熱搜榜上,有過這樣一個詞條,馬博發文訴德云社侵權,不夠熱也不夠爆,中間的位置,很快就消失了,不是8G
-
 法國暢銷書《唐詩之路》首次在國內出版 唐詩被外國作家讀出不同味道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的新書《唐詩之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部法國暢銷書首次在國內出版,唐詩被這位外國作家讀出了
法國暢銷書《唐詩之路》首次在國內出版 唐詩被外國作家讀出不同味道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的新書《唐詩之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部法國暢銷書首次在國內出版,唐詩被這位外國作家讀出了
-
 “黑客帝國”瞄向的不只是票房 定制和聯名產品亮相造熱度
時隔18年,黑客帝國憑借著第四部電影作品上映重新復出亮相。據燈塔專業版顯示,截至1月16日16時30分,電影《黑客帝國:矩陣重啟》的國內總
“黑客帝國”瞄向的不只是票房 定制和聯名產品亮相造熱度
時隔18年,黑客帝國憑借著第四部電影作品上映重新復出亮相。據燈塔專業版顯示,截至1月16日16時30分,電影《黑客帝國:矩陣重啟》的國內總
-
 電影《張之洞》“炮灰”式上映 強行上映太理想主義
2022年中國電影的第一個熱點事件,當屬電影《張之洞》1月7日上映首日僅賣出3張票,引發網友心疼。最終該片在上映第6天便悄悄下檔,總票房僅
電影《張之洞》“炮灰”式上映 強行上映太理想主義
2022年中國電影的第一個熱點事件,當屬電影《張之洞》1月7日上映首日僅賣出3張票,引發網友心疼。最終該片在上映第6天便悄悄下檔,總票房僅
-
 閱文名家研討會啟幕 擬覆蓋國內20所大學
1月12日,由中國作協機關報《文藝報》、中國現代文學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共同發起的閱文名家研討會正式啟幕,并在第一場活動中實現茅
閱文名家研討會啟幕 擬覆蓋國內20所大學
1月12日,由中國作協機關報《文藝報》、中國現代文學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共同發起的閱文名家研討會正式啟幕,并在第一場活動中實現茅
-
 10部影片定檔春節檔 今年能否再出“奇跡”創票房新高引關注
距2022年春節已不到20天,電影市場同樣摩拳擦掌。截至1月12日,定檔春節檔的影片共計10部,包括《奇跡·笨小孩》《四海》《喜羊羊與灰太狼
10部影片定檔春節檔 今年能否再出“奇跡”創票房新高引關注
距2022年春節已不到20天,電影市場同樣摩拳擦掌。截至1月12日,定檔春節檔的影片共計10部,包括《奇跡·笨小孩》《四海》《喜羊羊與灰太狼
-
 臘八你喝臘八粥嗎?天寒地凍冰雪愛好者期盼冬奧會
民謠有云:小孩小孩你別饞,過了臘八就是年。臘八過后,就拉開了過年的序幕。南北朝時期,將農歷十二月初八定為每年的臘日,祭祀祖先與天地
臘八你喝臘八粥嗎?天寒地凍冰雪愛好者期盼冬奧會
民謠有云:小孩小孩你別饞,過了臘八就是年。臘八過后,就拉開了過年的序幕。南北朝時期,將農歷十二月初八定為每年的臘日,祭祀祖先與天地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盤龍城工作站掛牌 推動文物考古事業發展
1月7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盤龍城工作站掛牌儀式,在盤龍城遺址博物院舉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經省委省政府研究同意組建,于2021年1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盤龍城工作站掛牌 推動文物考古事業發展
1月7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盤龍城工作站掛牌儀式,在盤龍城遺址博物院舉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經省委省政府研究同意組建,于2021年12
-
 “臘八”將至 這些臘八習俗你知道多少
民間有民謠:小孩兒你別饞,過了臘八就是年;臘八粥,喝幾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掃房子;二十五,凍豆腐;二十六,去買
“臘八”將至 這些臘八習俗你知道多少
民間有民謠:小孩兒你別饞,過了臘八就是年;臘八粥,喝幾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掃房子;二十五,凍豆腐;二十六,去買
相關內容
- 亞琦集團專注商貿物流十六載 攜手央視 打造中國民族強品牌
- 讓愛如期而至 全棉時代會員便捷服務「周期購」正式上線
- 冬奧場館“雪飛天”造雪工作啟動 將呈現“夢幻水晶”亮麗風景
- 冬奧場館“雪飛天”造雪工作啟動 將呈現“夢幻水晶”亮麗風景
- 近地天體望遠鏡發現近地小行星 將從255萬公里外飛掠過去
- 植物嫩芽頂部彎鉤發育形成機制 :重力是頂端彎鉤形成起始信號
- 植物嫩芽頂部彎鉤發育形成機制 :重力是頂端彎鉤形成起始信號
- 陜西河南部分地區有大雪 新一輪雨雪無縫銜接
- 陜西河南部分地區有大雪 新一輪雨雪無縫銜接
- 重達2000多噸!白鶴灘水電站水輪發電機組轉子順利完成吊裝
- 重達2000多噸!白鶴灘水電站水輪發電機組轉子順利完成吊裝
- “地球生物基因組計劃”全面測序 被稱為“下一個生物學登月計劃”
- “地球生物基因組計劃”全面測序 被稱為“下一個生物學登月計劃”
- 北京延慶兩座頒獎廣場完成首輪測試 確保冬奧會各項工作順利開展
- 北京延慶兩座頒獎廣場完成首輪測試 確保冬奧會各項工作順利開展
- 重要通知!冰雪京張·冬奧之城等10條線路為全國冰雪旅游精品線路
- 重要通知!冰雪京張·冬奧之城等10條線路為全國冰雪旅游精品線路
- 中青寶信息披露不完整 深圳證監局要求其責令改正
- 中青寶信息披露不完整 深圳證監局要求其責令改正
- 酒鬼酒2021年營業收入較上年同期增長86%左右
熱門資訊
-
 亞琦集團專注商貿物流十六載 攜手央視 打造中國民族強品牌
新年伊始,亞琦集團再次簽約央視,...
亞琦集團專注商貿物流十六載 攜手央視 打造中國民族強品牌
新年伊始,亞琦集團再次簽約央視,...
-
 讓愛如期而至 全棉時代會員便捷服務「周期購」正式上線
人間煙火色,最是新年時。新年禮一...
讓愛如期而至 全棉時代會員便捷服務「周期購」正式上線
人間煙火色,最是新年時。新年禮一...
-
 冬奧場館“雪飛天”造雪工作啟動 將呈現“夢幻水晶”亮麗風景
槍炮齊鳴,伴隨著11臺造雪設備一起...
冬奧場館“雪飛天”造雪工作啟動 將呈現“夢幻水晶”亮麗風景
槍炮齊鳴,伴隨著11臺造雪設備一起...
-
 冬奧場館“雪飛天”造雪工作啟動 將呈現“夢幻水晶”亮麗風景
槍炮齊鳴,伴隨著11臺造雪設備一起...
冬奧場館“雪飛天”造雪工作啟動 將呈現“夢幻水晶”亮麗風景
槍炮齊鳴,伴隨著11臺造雪設備一起...
-
 陜西河南部分地區有大雪 新一輪雨雪無縫銜接
我國天氣形勢將迎來轉折!1月20日至...
陜西河南部分地區有大雪 新一輪雨雪無縫銜接
我國天氣形勢將迎來轉折!1月20日至...
-
 近地天體望遠鏡發現近地小行星 將從255萬公里外飛掠過去
記者從中科院紫金山天文臺獲悉,該...
近地天體望遠鏡發現近地小行星 將從255萬公里外飛掠過去
記者從中科院紫金山天文臺獲悉,該...
-
 植物嫩芽頂部彎鉤發育形成機制 :重力是頂端彎鉤形成起始信號
春天,種子發出的嫩芽能夠以柔克剛...
植物嫩芽頂部彎鉤發育形成機制 :重力是頂端彎鉤形成起始信號
春天,種子發出的嫩芽能夠以柔克剛...
-
 北京延慶兩座頒獎廣場完成首輪測試 確保冬奧會各項工作順利開展
1月15日,延慶頒獎廣場舞臺燈光音...
北京延慶兩座頒獎廣場完成首輪測試 確保冬奧會各項工作順利開展
1月15日,延慶頒獎廣場舞臺燈光音...
-
 “地球生物基因組計劃”全面測序 被稱為“下一個生物學登月計劃”
全球范圍內繪制所有已知植物、動物...
“地球生物基因組計劃”全面測序 被稱為“下一個生物學登月計劃”
全球范圍內繪制所有已知植物、動物...
-
 重要通知!冰雪京張·冬奧之城等10條線路為全國冰雪旅游精品線路
1月18日,文化和旅游部發布關于公...
重要通知!冰雪京張·冬奧之城等10條線路為全國冰雪旅游精品線路
1月18日,文化和旅游部發布關于公...
-
 酒鬼酒2021年營業收入較上年同期增長86%左右
1月18日晚間,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酒鬼酒2021年營業收入較上年同期增長86%左右
1月18日晚間,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
 數據顯示:今年1月上旬白酒價格環比漲0.14% 名酒價格上漲0.12%
1月18日,北京商報記者獲悉,瀘州...
數據顯示:今年1月上旬白酒價格環比漲0.14% 名酒價格上漲0.12%
1月18日,北京商報記者獲悉,瀘州...
-
 社區生鮮市場加速洗牌 錢大媽一路狂奔掉進“內卷”
社區、生鮮、零售,每個行業進行著...
社區生鮮市場加速洗牌 錢大媽一路狂奔掉進“內卷”
社區、生鮮、零售,每個行業進行著...
-
 社區生鮮市場加速洗牌 錢大媽一路狂奔掉進“內卷”
社區、生鮮、零售,每個行業進行著...
社區生鮮市場加速洗牌 錢大媽一路狂奔掉進“內卷”
社區、生鮮、零售,每個行業進行著...
-
 央行:降準仍有一定空間 房地產信貸等有所改善
近期,房地產銷售、購地、融資等行...
央行:降準仍有一定空間 房地產信貸等有所改善
近期,房地產銷售、購地、融資等行...
文章排行
最新圖文
-
 臘八你喝臘八粥嗎?天寒地凍冰雪愛好者期盼冬奧會
民謠有云:小孩小孩你別饞,過了臘...
臘八你喝臘八粥嗎?天寒地凍冰雪愛好者期盼冬奧會
民謠有云:小孩小孩你別饞,過了臘...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盤龍城工作站掛牌 推動文物考古事業發展
1月7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盤龍...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盤龍城工作站掛牌 推動文物考古事業發展
1月7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盤龍...
-
 “臘八”將至 這些臘八習俗你知道多少
民間有民謠:小孩兒你別饞,過了臘...
“臘八”將至 這些臘八習俗你知道多少
民間有民謠:小孩兒你別饞,過了臘...
-
 “數字藏品”熱潮來襲 首款網文IP數字藏品上線即被售空
繼游戲、虛擬偶像、電競等之后,元...
“數字藏品”熱潮來襲 首款網文IP數字藏品上線即被售空
繼游戲、虛擬偶像、電競等之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