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95”后新農人的無悔選擇
四年前的這個時候,23歲的李益已經是一家大型連鎖超市合伙人店長,張兩廣正在一家互聯網營銷公司實習,沈笑芬則想著在廣州“找個公司,好好工作”。
同是1996年出生的他們,2019年下半年不約而同回到各自老家當起了新農人,為家鄉村民提供生產托管服務。如今,李益成了高州市農業托管服務中心負責人,張兩廣當選廣東首屆十大農業生產最美生產托管員,沈笑芬則在廣東省水稻機收減損技能大比武活動廣州賽區斬獲亞軍。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號角,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聚在了一起;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的事業,又讓這些年輕人愈發覺得“大有可為”。他們為什么放棄城市的優渥收入回到農村?他們經歷了哪些迷茫與困惑?他們又如何不斷突破自己、讓千萬農戶搭上現代農業快車?
 【資料圖】
【資料圖】
不約而同的選擇
一年好景看春耕。3月1日早上8點,身材嬌小的沈笑芬熟練地駕駛著一輛五噸重的拖拉機,在地里來回穿梭耙田。兩小時后,父親沈燦星用皮卡車拉來三桶柴油,給這個大家伙加油。這也是沈笑芬一上午難得的閑暇時間。
12點半,眼前的三十畝地被完整耕了一遍。沈燦星看著女兒感慨:“我小時候父親用牛耕地,一小時才能耕一兩分地;后來我用手扶拖拉機,一小時能耕三分地;現在這臺拖拉機,一小時能耕七八畝。”
沈燦星是個擅長駕駛各種農機的“土專家”,多年來一直為鄉親們提供農機服務。2019年畢業前的一天,沈笑芬回到家突然發現,父親的白頭發多了不少。“那時才發現爸爸真的老了。”沈笑芬說,“當時就下定決心要回老家來幫他。”
從此,增城石灘鎮的田間地頭,多了一個靚麗的身影。在父親的幫助下,沈笑芬上手很快,無論是拖拉機、收割機、插秧機、無人機,她都游刃有余。“我還是很有天賦的!”沈笑芬調侃到。
四年過去,“沈家農機隊”變成了廣州市增城石鄉農機專業合作社。一家五姐弟陸續全都回到家鄉,一同做起了“新農人”。他們還主導聯動周邊村鎮的多家農機合作社,成立了廣州首家農機聯合社。目前,聯合社服務的種植面積超過了10萬畝次。
“沈家農機隊”的快速發展,乘上了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推廣的東風。2017年8月,農業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聯合印發《關于加快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的指導意見》提出,把發展農業生產托管作為推進農業生產性服務業、帶動普通農戶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的主推服務方式。
沈笑芬等人選擇返鄉的2019年下半年,廣東也已開始醞釀組織實施農業生產托管項目。2020年開始,廣東投入財政資金5億元,以服務補貼為載體培育托管服務市場。
近年來,廣東農業服務業增加值保持著10%以上的增速,在農業總產值中的占比從2018年的4.3%上升為2022年上半年的5.2%,無論是增速還是在農業總產值的占比都快速增長,遠遠高于農林牧副漁總產值增長。
張兩廣大學讀的農產品營銷專業,上學時就對北方地區的農業生產托管試點有所了解。大學畢業后,村支書希望他回鄉報考大學生村官。
“村里的合作社支持我讀的大學,我肯定要回去。”那時,他已經在實習的互聯網營銷公司做到了經理崗位,月薪兩萬。一個月后,張兩廣回到了茂名市電白區譚儒村,“現在農村更需要我,農業生產托管大有可為!”
李益則是一開始就想著要回家鄉工作的。他的家鄉高州是遠近聞名的水果之鄉。父親李子文是高州市子文水果專業合作社負責人,也是當地小有名氣的種果高手。
大學畢業后,李益進入了永輝超市,不到兩年就當上了合伙人店長。在這期間他系統學習了農產品供應鏈經驗。返鄉后,他發起成立了高市農業生產托管服務中心,為農戶提供“保姆式”管理,讓不懂技術、不想管地的農戶也能獲得豐產豐收。
迷茫與困境
萬事開頭難,盡管內心有所準備,但回到農村第一年的困難遠遠超過了沈笑芬的想象。很多人一開始不理解托農業生產管的意義和價值,寧愿撂荒也不愿意把土地托管出來。
“比如一個農戶有5畝地要整耕,直接派人去做效率很低利潤很少,但如果農戶發動同村人一共50畝地一起,把小田整合成大田,生產效率就上來了。”張兩廣說,但是一條自然村一般有同族親戚關系,外人往往很難去整合土地。
李益原本以為有父親打下的基礎,返鄉后的工作會從容一些,每天可以睡得安逸一些。然而面對緊迫的工作進度,他經常晚晚失眠,在朋友圈感嘆“自己還是太年輕了”。
托管服務實際上要賺取農戶的服務費,才能生存。最開始,果農并不樂意將果園交出去。為了打消農戶的疑慮,李益根據果園管理狀況,承諾每年給農戶600—900元/畝的保底收益;水稻田則承諾每年給農戶550—600元/畝的保底收益。扣除合作社的服務費和農戶的保底收益后,剩余的收益則五五分成。保底性收益,給農戶吃下了定心丸。
“一開始只是抱著幫助父親的想法。”后來沈笑芬發現,日益空心化的鄉村,土地撂荒現象嚴重,“想通過農業生產托管幫助更多農民。”
然而,這一過程并不容易。在一次維修拖拉機換耙刀時,沈笑芬手掌不慎被割開一道口子,縫了18針,留下一條清晰可見的傷口。
由于常年在室外干活,以前家里最白的沈笑芬如今成了“黑妹”。“第一年是最難熬的。”她一開始操作的耕田機空調是壞的,夏天駕駛室的溫度經常三四十度,一上去就冒出豆大的汗珠,“好幾次都中暑了,休息一會兒就繼續干!”
父親沈燦星得知后心疼不已。但沈笑芬覺得,既然選擇了就要堅持。正是憑借著著一股韌勁,返鄉一年多后,她獲得了廣東省水稻機收減損技能大比武活動(廣州賽區)第2名,“滿滿的成就感,最艱難的時候過去了。”
張兩廣剛返鄉時,也感受到了巨大的落差。“第一個月到手工資才1400,不到之前的十分之一。”張兩廣說,盡管一開始收入“少得可憐”,但他一直相信,是金子在哪里都會發光。
村里有一位老人家里勞動力不足,當時還是貧困戶,張兩廣知道后用機器去幫他收割水稻,對方慢慢看到了農業生產托管的價值,“不用下地也能種糧”。
后來張兩廣每次經過老人家門口,老人都會拿著家里的番薯或芋頭給他,“這些發自內心的感謝,讓我覺得這份工作更有意義了。”
突圍與帶動
這些在大城市學習工作過的年輕人,回到家鄉從事農業生產托管服務,往往能發揮更大的價值。他們把其他行業的知識和經驗帶到了農業,推動了當地農業現代化乃至智能化進程。
張兩廣返鄉后,既是村干部,又是農機手和托管員。在他的幫助下,譚儒合作社共整村推進19條村的生產托管服務,服務農戶超1268戶。
張兩廣還將書本上的知識學以致用,創辦電商團隊,幫助農戶銷售農作物。據統計,他帶領的電商團隊銷售額超260萬元。
高州是廣東省最大的荔枝龍眼生產基地之一,但很多農戶由于年紀大了,沒有精力去管理,或者管理措施不當,導致收成不高。李益看到家鄉有些果園荒廢山間,無人看管,很是可惜。
“對于荔枝、龍眼來說,技術真的太重要了。”李益說,在高州市沙田鎮那敢村,有一片龍眼園由子文合作社常年打理,每年產量有2000斤/畝,而之前管理不當時產量只有800斤/畝。除了產量,最重要的是龍眼品質的改變。之前,果子小、病害多,而現在個頭大、顏色靚,售價每斤一般比周邊果園能高一塊錢。
為了帶動更多農戶精心種果,并推廣托管服務效果,子文合作社建設了750畝示范基地。“很多農戶不相信托管可以帶來更大的收益,也不放心把自己手上的土地交給其他人管,我們建立示范基地的目的就是要讓農戶親眼看見效果,這樣他們才會慢慢信任這項服務。”李益說。
越來越多的村民認識到,把專業的事交給專業的人做,更有利于降低農業生產成本,實現穩產增收。除了果園托管服務外,李益還承接了撂荒地水稻的復耕復種業務,成為高州市農業托管服務中心負責人。
四年過去,不止沈笑芬,一家五兄弟姐妹陸陸續續全都回到家鄉,一同做起了新農人。在深圳做過6年品牌推廣的大姐沈燕芬出任“CEO”;學外貿的二姐沈桂芬管起了財務和行政;學管理的三哥沈智威負責后勤保障;排行第四的沈笑芬則和五弟沈智豪負責一線工作。他們晚上在20分鐘車程外的增城城區生活,每天八點左右到合作社“上班”。
憑借著年輕人的新思維,五姐弟成立的農機聯合社聘請熟練農機手,開拓了“全程機械化+綜合農事”服務模式,還打造了自己的增城絲苗米品牌,降低了產品生產成本,提高了產品附加值,讓農民放心地將耕種和產銷全流程交給合作社托管,近一年來服務農戶超1800戶。
“我們還可以免費開展農機培訓,二三十天后就可以自己操作,月入上萬不是問題。”沈笑芬說,現在農村最缺農機手,只要有年輕人肯干,農村是大有可為的。
現在,五姐弟正在設計一個集農業生產管理、運營管理、設備管理、人資管理于一體的智能化的運營系統,可以指導新農人進行及時澆水、施肥,還可以隨時查看每一塊田的生長情況,積累農田信息與生產數據,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產效率。
2022年除夕夜,沈笑芬在朋友圈上寫下一段95后新農人的新年寄語:“小時候,我們是童年的玩伴、吵鬧的冤家;長大后,我們是工作上的搭檔、沈家農機隊的一員。我們與千萬熱血青年一般,有向往的生活,憧憬著詩和遠方,不曾想,機緣巧合下,因鄉村振興的浪潮,我們再次被推到了一起。現在我們重新組合,這是我們走出舒適圈的第一步,是我們振興鄉村的第一關。我們每一個人,各有特點各有專長,各司其職各盡所能,缺一不可,每個人都很重要!”
免責聲明:本文不構成任何商業建議,投資有風險,選擇需謹慎!本站發布的圖文一切為分享交流,傳播正能量,此文不保證數據的準確性,內容僅供參考
關鍵詞:
-
 三個“95”后新農人的無悔選擇
四年前的這個時候,23歲的李益已經是一家大型連鎖超市合伙人店長,張兩廣正在一家互聯網營銷公司實習,沈笑芬則想著在廣州“找個公司,...
三個“95”后新農人的無悔選擇
四年前的這個時候,23歲的李益已經是一家大型連鎖超市合伙人店長,張兩廣正在一家互聯網營銷公司實習,沈笑芬則想著在廣州“找個公司,...
-
 東莞市中心多了座公益籃球場-環球速訊
新快報訊記者高京報道昨天上午,耐撕街頭空間公益籃球場在東莞市中心位置正式亮相。接下來市民不僅可以在這里免費打球,還將有機會參與...
東莞市中心多了座公益籃球場-環球速訊
新快報訊記者高京報道昨天上午,耐撕街頭空間公益籃球場在東莞市中心位置正式亮相。接下來市民不僅可以在這里免費打球,還將有機會參與...
-
 全面恢復長途服務!香港西九龍直通北京等全國66個站點-今日看點
4月1日,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全面恢復長途跨境列車服務,直通北京、天津、重慶、長沙等全國66個站點,列車班次也增加到164列。深圳邊檢總站西九
全面恢復長途服務!香港西九龍直通北京等全國66個站點-今日看點
4月1日,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全面恢復長途跨境列車服務,直通北京、天津、重慶、長沙等全國66個站點,列車班次也增加到164列。深圳邊檢總站西九
-
 廣東常住人口穩居全國第一,連續三年出生人口超百萬
文 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陳澤云繼近日發布2022年統計年報之后,4月2日,廣東省統計局發布數據分析稱,廣東是全國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同時達到過億
廣東常住人口穩居全國第一,連續三年出生人口超百萬
文 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陳澤云繼近日發布2022年統計年報之后,4月2日,廣東省統計局發布數據分析稱,廣東是全國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同時達到過億
-
 廣東明日夜間起或迎新一股冷空氣 可改善“回南天”
雖帶來強對流天氣但可改善“回南天”羊城晚報訊記者梁懌韜報道:氣象部門預計,4日夜間起廣東將迎來新一股冷空氣。雖然該股冷空氣將再次...
廣東明日夜間起或迎新一股冷空氣 可改善“回南天”
雖帶來強對流天氣但可改善“回南天”羊城晚報訊記者梁懌韜報道:氣象部門預計,4日夜間起廣東將迎來新一股冷空氣。雖然該股冷空氣將再次...
-
 深圳工業增加值躍居全國第一 工業強市爭創“小巨人”-天天熱點評
廣東擁有867家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位居全國第二文 表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許張超如今的中國制造已經成為一張響當當的名片。在...
深圳工業增加值躍居全國第一 工業強市爭創“小巨人”-天天熱點評
廣東擁有867家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位居全國第二文 表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許張超如今的中國制造已經成為一張響當當的名片。在...
-
 全國畢業生找工作,為何青睞大灣區?
全國多所高校發布2022屆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孫唯實習生鄭若彤小喬來到深圳已經六個月了。2021年從甘肅某一本院校畢業后,小
全國畢業生找工作,為何青睞大灣區?
全國多所高校發布2022屆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孫唯實習生鄭若彤小喬來到深圳已經六個月了。2021年從甘肅某一本院校畢業后,小
-
 廣東2023年春季高考錄取開始 “3+證書”本科批次依舊火熱
羊城晚報訊記者孫唯報道:廣東2023年春季高考招生錄取時間為3月29日至4月7日。3月29日,普通高等學校招收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統一考試(“3+證
廣東2023年春季高考錄取開始 “3+證書”本科批次依舊火熱
羊城晚報訊記者孫唯報道:廣東2023年春季高考招生錄取時間為3月29日至4月7日。3月29日,普通高等學校招收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統一考試(“3+證
-
 清明節當天高速免費 廣東部分收費站或明顯擁堵-全球聚看點
羊城晚報訊記者王丹陽、通訊員粵交綜報道:3月31日,記者從廣東省交通運輸廳獲悉,今年踏青祭祖的需求或大幅增長,且清明僅有1天假期,預計清
清明節當天高速免費 廣東部分收費站或明顯擁堵-全球聚看點
羊城晚報訊記者王丹陽、通訊員粵交綜報道:3月31日,記者從廣東省交通運輸廳獲悉,今年踏青祭祖的需求或大幅增長,且清明僅有1天假期,預計清
-
 賽出職企同心!廣東省集體協商競賽圓滿結束
文 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侯夢菲通訊員傅敬忠圖 通訊員林景余3月31日,廣東省集體協商競賽在廣州圓滿結束。該競賽以“粵協商、粵和諧、粵...
賽出職企同心!廣東省集體協商競賽圓滿結束
文 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侯夢菲通訊員傅敬忠圖 通訊員林景余3月31日,廣東省集體協商競賽在廣州圓滿結束。該競賽以“粵協商、粵和諧、粵...
相關內容
- 三個“95”后新農人的無悔選擇
- 【光明時評】保護未成年人,既要有力度也要有智慧
- 西鳳375酒第一屆全民健康跑全面啟動
- 義診檢查發現乳腺腫瘤,患者點贊省立醫院幫扶很實在
- 江蘇徐州市減災辦發布重要天氣應對工作提示-今日快看
- 考研英語多少分能過線?考研時英語需要過幾級?
- 考研學碩報名的時候需要注意什么?考研選學碩好還是選專碩好?
- 考研有政審環節嗎?考研的具體流程是什么?
- 王稽棄市案_關于王稽棄市案介紹-全球聚看點
- 中銀E貸提款未到賬怎么辦?中銀E貸的錢能取出來嗎?
- 新股漲跌有什么限制?新股網上申購的規則是什么?
- 凈值型理財產品投資的標準是什么?凈值型理財產品怎么分類?
- 九方財富公布2022年度業績,凈利潤增長98.2%,新戰略布局值得關注
- 千嘉科技終止創業板IPO-環球即時看
- 當日快訊:江蘇陽光等50股獲陸股通增倉超100%-世界要聞
- 當日快訊:354股獲券商買入評級,保利發展目標漲幅達76.93%
- 當日快訊:暴雨藍色預警:10省區市將現大到暴雨,湖北湖南等地有大暴雨
- 當日快訊:3月財新中國制造業PMI錄得50.0,回落1.6個百分點-世界通訊
- 當日快訊:洪都拉斯華僑代表舉行升旗儀式,擁護中洪兩國建交-天天實時
- 護林員常態化巡護 上千只蒼鷺在四川廣元“安家”
熱門資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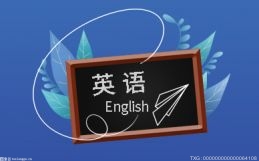 考研英語多少分能過線?考研時英語需要過幾級?
考研英語多少分能過線?考研英語二...
考研英語多少分能過線?考研時英語需要過幾級?
考研英語多少分能過線?考研英語二...
-
 考研學碩報名的時候需要注意什么?考研選學碩好還是選專碩好?
考研學碩報名的時候需要注意什么?...
考研學碩報名的時候需要注意什么?考研選學碩好還是選專碩好?
考研學碩報名的時候需要注意什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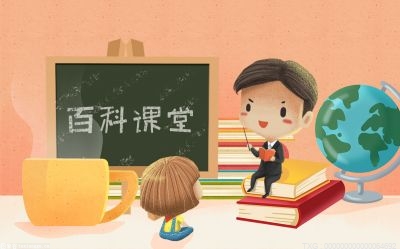 考研有政審環節嗎?考研的具體流程是什么?
考研有政審環節嗎?考研是有政審環...
考研有政審環節嗎?考研的具體流程是什么?
考研有政審環節嗎?考研是有政審環...
-
 九方財富公布2022年度業績,凈利潤增長98.2%,新戰略布局值得關注
3月30日,剛剛登陸港交所主板市場...
九方財富公布2022年度業績,凈利潤增長98.2%,新戰略布局值得關注
3月30日,剛剛登陸港交所主板市場...
-
 陜西平利: “小工程”解決鄉村治理“大問題”-當前簡訊
作者:本報記者張哲浩李潔本報通訊...
陜西平利: “小工程”解決鄉村治理“大問題”-當前簡訊
作者:本報記者張哲浩李潔本報通訊...
-
 特色經濟持續發力 消費加速復蘇-當前滾動
央視網消息:四月春意盎然,百花盛...
特色經濟持續發力 消費加速復蘇-當前滾動
央視網消息:四月春意盎然,百花盛...
-
 護林員常態化巡護 上千只蒼鷺在四川廣元“安家”
隨著天氣一天天轉暖,一些鳥類也開...
護林員常態化巡護 上千只蒼鷺在四川廣元“安家”
隨著天氣一天天轉暖,一些鳥類也開...
-
 千嘉科技終止創業板IPO-環球即時看
據深交所網站3月31日消息,深交所...
千嘉科技終止創業板IPO-環球即時看
據深交所網站3月31日消息,深交所...
-
 河南項城: “一鍵呼叫”讓群眾搭上就醫“直通車”-天天熱門
“呼叫集團院區,我是永豐片區閆莊...
河南項城: “一鍵呼叫”讓群眾搭上就醫“直通車”-天天熱門
“呼叫集團院區,我是永豐片區閆莊...
-
 我國新收集農作物種質資源12.4萬份
新華社三亞4月2日電(記者羅江、陳...
我國新收集農作物種質資源12.4萬份
新華社三亞4月2日電(記者羅江、陳...
-
 專訪梨花教育繳費8800教育張弛:不斷探索聲音的價值
伴隨著5G時代全面到來,抖音、快手...
專訪梨花教育繳費8800教育張弛:不斷探索聲音的價值
伴隨著5G時代全面到來,抖音、快手...
-
 帶押過戶有什么優點?帶押過戶房貸利率會改變嗎?
帶押過戶有什么優點?帶押過戶縮短...
帶押過戶有什么優點?帶押過戶房貸利率會改變嗎?
帶押過戶有什么優點?帶押過戶縮短...
-
 居民養老和職工養老能不能合并?居民養老和職工養老能退一個嗎?
居民養老和職工養老能不能合并?如...
居民養老和職工養老能不能合并?居民養老和職工養老能退一個嗎?
居民養老和職工養老能不能合并?如...
-
 基金強制退市需要什么條件?基金清盤散戶可以拿回自己的錢嘛?
基金強制退市需要什么條件?【1】...
基金強制退市需要什么條件?基金清盤散戶可以拿回自己的錢嘛?
基金強制退市需要什么條件?【1】...
-
 整體上市有哪些優點?整體上市的缺點是什么?
整體上市有哪些優點?①整體上市符...
整體上市有哪些優點?整體上市的缺點是什么?
整體上市有哪些優點?①整體上市符...
文章排行
最新圖文
-
 廣東2023年春季高考錄取開始 “3+證書”本科批次依舊火熱
羊城晚報訊記者孫唯報道:廣東2023...
廣東2023年春季高考錄取開始 “3+證書”本科批次依舊火熱
羊城晚報訊記者孫唯報道:廣東2023...
-
 清明節當天高速免費 廣東部分收費站或明顯擁堵-全球聚看點
羊城晚報訊記者王丹陽、通訊員粵交...
清明節當天高速免費 廣東部分收費站或明顯擁堵-全球聚看點
羊城晚報訊記者王丹陽、通訊員粵交...
-
 賽出職企同心!廣東省集體協商競賽圓滿結束
文 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侯夢菲通訊...
賽出職企同心!廣東省集體協商競賽圓滿結束
文 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侯夢菲通訊...
-
 廣東天氣:清明節前雨紛紛,或有“回南”來為難-世界速訊
文 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梁懌韜通訊...
廣東天氣:清明節前雨紛紛,或有“回南”來為難-世界速訊
文 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梁懌韜通訊...